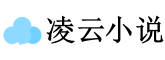庆历三月初三,龙抬头。
一艘大船在江南水师的护航下,缓缓靠拢了码头,船上抛锚放绳,校官们极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,紧接着,被做成阶梯模样的跳板被搁在了码头与甲板之间,岸上的吏员们赶紧铺上厚布,以免脚滑。
天边远远滚过一帘春雷,迸迸作响,似乎是在欢迎钦差大人的到来,而同一时间,码头上也是鞭炮齐鸣,锣鼓喧天,岸涂之上备好的冲天雷也被依次点燃,炮声大作,竟将老天爷的声威都掩了下去。
码头上的官员们皱眉,却不好意思捂耳朵,只将目光投注在跳板之上。
不一时,一位年青的官员出现在甲板之上,领着一行侍卫沉默了下了船,分列成两行。
又过了一会儿,一位穿着一袭紫色官服的年轻英俊官员,才微笑着走了出来,只见此人在官服之外套了件鹤氅,白素的颜色顿时冲淡了官服深紫所带来的视觉刺激,让码头上众人的目光,都被他那张温和亲切而清秀无比的面容吸引了过去。
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穿紫色的官服,码头上众官员心知,被己等“千呼万唤”的钦差大人范提司。便是眼前这人,下意识里往前挤了两步,举手欲揖。
范闲却没有急着阻止众人行礼。反而将手往旁边一伸,握住平空伸出的一只小手,牵着一个小男孩儿并排站在甲板上,踏着梯子。往船下行来。
小男孩儿地身上穿着一袭淡黄色的常服袍衫,领子处露出一圈毛衫的绒毛,衫子上绣着一对可爱却不知名地灵兽,配着那张清美的面容,灵动的双眼,看着煞是可爱。
众官员却是心中一惊,知道这位便是被皇上赶到范提司身边的三皇子,赶紧调整方向。齐齐对三皇子行礼:“江南路众官员,见过殿下。”
三皇子笑着点了点头,用雏音未去地声音说道:“天气寒冷,诸位大人辛苦了,我只是随老师前来学习,不需多礼。
被老师二字提醒的众官员们赶紧又对范闲行礼,连道大人远来辛苦。如何云云。
行礼之余,几十位官员偷瞄着从船上走下来的这两个男子。发现对方年龄虽然相差不少,但面容却是极为相似,站在岸边,江风将这两名男子的衣衫下摆吹动,在清贵之气显露十足之余,更是透着股难得的和谐与脱尘之意。
众人不免开始在肚子里猜疑。看来那个关于范提司的身世流言,只怕是真的了……一念及此。心中又开始忐忑,不知道己等先向三皇子行礼,会不会让范闲心中不愉,毕竟对方才是正主儿,而且钦差大臣的身份,依朝制而论,可是要比未成年地皇子要金贵太多。
范闲哪里有这么多的想法,他望着码头上这些面目陌生的官员,脸上堆起最亲切的笑容,一一含笑应过,又着力将对方的官职与官名记下来,扮足了一位政治新星所应有的礼数与自矜。
范提司携皇子下江南,这是大事,所以今天来码头迎接的官员人数极多,文官方面有江南路总督府巡抚这方地直属官员,又有苏杭两州的知州各领着两拔人,相隔较远地几个州知州虽不敢擅离辖境来迎接,但州上通判,理同等级的官员还是来了不少,另又有江南盐路转运司的官员,武官方面自然少不了江南水师的守备参将之流,当然,如今身为范闲直属下属的内库转运司更是人员来的都极齐。
总之林林总总,加起来已近百人,整个江南路地父母官们只怕一大半都挤到了码头上,若东夷城偷了监察院三处的火药,在这儿弄个响儿,整个庆国最富庶地江南路恐怕会在一天之内陷入瘫痪之中。
码头上范闲满脸微笑与众官员见礼,问题是只见人头攒动,官服混杂,大冬天里汗味十足,一张张陌生而谄媚的面容从自己的眼前晃过,哪里还认的清到底谁是谁?而这些官员们却是不知道他内心的感受,看着小范大人面上笑容未减,越发觉得是自己这一路上送的礼起到了效果,大着胆子往他与三皇子的身边挤,怎的也要寒喧两句,套个近乎,才对得起送出去的银子啊!
那些离大江稍远的州县官员却一直没有寻到机会送礼,所以心气儿也不是那么足,带着两丝艳羡,三分嫉恨地在人群外侧看着里面的同僚不堪地拍着马屁。
一时间码头上马屁臭不堪闻,范闲被剃的干干净净的下颌也被着力摸了无数下,好不热闹,渐渐官员们说的话愈发不堪起来,尤其是苏州府知州那一路官员,乃是从太学出来的系统中人,非要依着范闲如今兼任太学司业的缘故,口口声声喊着……范老师!
范闲强抑心头厌烦,坚不肯受,开玩笑,自己年不过二十,就要当一任知州的老师……传回京都去,只怕要被皇帝老子笑死!而三皇子被他牵着小手,忍着身边无耻的话语,心里也是不痛快,暗想小范大人乃是本人的老师,你们这些老头子居然敢和我抢?小孩子终于忍受不了,冷着脸咳了两声。
咳声一出,场间顿时冷场,杭州知州是个见机极快的老奸滑,暗喜苏州知州吃瘪,却正色说道:“今日天寒,我看诸位大人还是赶紧请钦差大人还有殿下上去歇息吧。”
此言一出,范闲与三皇子心中甚慰。同时间向杭州知州投去了欣赏的目光,杭州知州被这目光一扫,顿时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好不舒服。就像是吃了根人参一般。
……
……
歇息?没那么容易,就算诸位官员稍微退开之后,相关地仪仗依然耗了许多时间,范闲与殿下才被众位官员拱绕着往岸上的斜坡走去。坡
上有一大大的竹棚,看模样还挺新,估计没搭几天,是专门为了范闲下江南准备地。
走上斜坡,竹棚外已经有两位身着紫色官服的大官,肃然等候在外,范闲一见这二人,便拉着三皇子的手往那处赶了几步。以示尊敬。
这两位官员身份不一般,一位乃是江南路总督薛清薛大人,一位乃是巡抚戴思成戴大人。
在庆国的官场上有句话叫做:一宫,二省,三院,七路。一宫自然是皇宫,二省便是如今并作一处办理政务地门下中书省。三院便是监察院、枢密院、教育院,只是教育院已然在庆历元年的新政之中裁撤为太学、同文阁、礼部三处职司。
而这句话最后的七路。指的便是庆国如今地方上分作七大路,各路总督代天子巡牧一方,而且如今庆国路州之间郡一级的管理职能已经逐渐淡化,一路总督在军务之外,更开始直接控制辖下州县,权力极大。是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。
皇帝陛下当然要挑选自己最信任的亲信担任这个要紧职务,而且总督在能力方面也是顶尖的强悍。
与总督地权力气焰相比。巡抚偏重文治,但份量却要轻了太多。
如果以品秩而论,总督是正二品,巡抚是从二品,不算特别高的级别,但是庆国皇室为了方便这七路的总督专心政务,少受六部掣肘,一直以来的规矩都会让一路总督兼协办大学士,都察院右都御史或是兵部尚书衔,这便是从一品的大员了,面对着朝中宰相中书,也不至于没有说话的份量。
而江南乃是庆国重中之重,如今的江南路总督薛清又深得陛下信任,所以竟是直接兼地殿阁大学士,乃地地道道的正一品超级大员!
以薛清地身份地位,就算是范闲与三皇子也不敢有丝毫轻慢,所以加快了脚步。
但到了竹棚之外,范闲只是用温和的眼光看了薛清一眼,并没有先开口讲话。这是规矩,薛清与戴思成明白,对方乃是钦差大臣,自己就算再如何权高位重,也要先向对方行礼,这不是敬范闲,也不是敬皇子,而是敬……陛下。
摆香案,请圣旨,亮明剑,竹棚之内官员跪了一地,行完一应仪式之后,范闲赶紧将面前的江南总督薛清扶了起来,又转身扶起了巡抚大人,这才领着三皇子极恭谨地对薛清行礼。
薛清的身份当得起他与三皇子之深深一揖,但这位江南总督似乎没想到传说中的范提司,并没有一丝年青权臣及文人的清高气,甘愿在小处上抹平,眼中闪过一抹欣赏。
巡抚站在一旁,赶紧半侧了身子回礼。薛清也不会傻不拉叽地任由面前这“哥俩儿”将礼行完,早已温和扶住了两人,说道:“范大人见外了。”
范闲一怔,再看旁边地小三儿对着薛清似乎有些窘迫,更是讷闷。
薛清微笑说道:“本官来江南之前,在书阁里做过,所谓学士倒不全是虚秩,三殿下小的时候,常在本官身边玩耍……只是过去了好几年,也不知道殿下还记不记得。”
三皇子苦笑一声,又重新向薛清行了个弟子礼,轻声说道:“大人每年回京述职,父皇都令学生去府上拜礼,哪里敢忘?”
范闲有些糊涂,心里细细一品,越发弄不清楚京都里那位皇帝究竟在想什么。正想着,又听着薛清和声说道:“说来我与范大人也有渊源。”
范闲在这位大官面前不好卖乖,好奇问道:“不瞒大人,晚生确实不知。”
薛清喜欢对方直爽,笑着捋须说道:“当初本官中举之时,座师便是林相。论起辈份来,你倒真要称我一声兄了。”
范闲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,不过对方如今已经贵为一方总督。那些往年情份自然也只是说说而已,而且他再脸厚心黑胆大,也不好意思顺着这个杆儿爬,与总督称兄道弟?自己手头地权力是够这个资格。可是年纪资历……似乎差的远了些。
一行人在草棚里稍歇,范闲与薛清略聊了聊沿路见闻,薛清眉头微皱,又问陛下在京中身体可好,总之都是一些套话废话,不过也稍拉近了些距离,稍熟络了些。范闲看着这位一品大员,发现对方清瞿面容里带着一丝并未刻意掩饰地愁容。稍一思忖,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身为江南总督,地盘里却忽然出现了一位要常驻的钦差大臣,这事儿轮到哪一路的总督身上,都不好受,更何况这位钦差大臣要接手内库,只怕要与京里地贵人们大打出手。总督虽然权高位重,又深受陛下信任。但夹在中间,总是不好处的。
薛清举起茶杯轻轻饮了一口,有意无意间问道:“小范大人这两年大概就得在江南辛苦了,虽说是陛下信任,但是江南不比京都,虽然繁华却终究不是长留之地……再过两年。我也要向陛下告老,回京里坐个钓鱼翁……能多亲近亲近皇上。总比在江南要好些。”
范闲听出对方话里意思,笑着迎合道:“大人代陛下巡牧一方,劳苦功高。”
薛清微笑说道:“小范大人可定好了住在哪处?这苏州城里盐商不少,他们都愿意献出宅子,供大人挑选。”
盐商之富,天下皆知,他们双手送上的宅子那会豪奢到什么程度,范闲不问而知,他却话风一转问道:“这太过叼扰也是不好,而且传回京里,晚生总有些惴惴。”他说的直爽,惹得薛清摇头直笑,心想诗家就有这椿不好,做什么事都要遮掩,怎么你在江上收银子时却不遮掩一下。
范闲很诚恳地问道:“烦请大人指教,往年地内库转运司正使……怎么安排?”
薛清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,说道:“范大人,你的身份可不比往年的内库转运司正使。要说安排,内库拟定的官宅远在闽
地,不过这十几年也没有哪位正使大人真的去住过,就那你前任黄大人来说,他就长年住在……信阳。”
说到信阳二字时,这位江南总督有意无意看了范闲一眼。
范闲微微皱眉说道:“可以不住在朝廷安排的官邸?”
这话似是疑惑,似是试探。
薛清点了点头。
范闲笑着说道:“不敢瞒老大人,我这个月一直住在杭州,没有前来苏州拜访大人,是本人的不是……不过那处宅子倒真是不错,如果可以自己选的话,我当然愿意住在杭州了。”
薛清微微一怔,没想到对方提出要住在杭州,看着范闲地双眼有那么一阵子沉默,似乎在猜想这位当红的年轻权臣所言是真是假,江南总督府在苏州,他最忌讳的当然就是范闲也留在苏州,不说干扰政务,只说这两头齐大的局面,江南路的官员们都会头痛不已,对于自己处理事务,大有阻碍。
他瞧着范闲诚恳的面容,眼中闪过一抹异色,微笑说道:“自然无妨,范大人想住哪里,就住哪里。”
范闲呵呵一笑说道:“当然,就算住在杭州,也少不得要常来苏州叨扰大人几顿,听说大人府上用的是北齐名厨,京都人都好生羡慕,我也想有这口福。”
薛总督哈哈大笑道:“本官便是好这一口,没想到范大人也是同道中人,何须再等以后,今天晚上诸位同僚为大人与殿下备好了接风宴,是在江南居,明天我便请大人来家中稍坐。”
得了范闲暗中不干涉他做事地承诺,这位江南总督难以自抑的放松起来。
这几声大笑马上传遍了竹棚内外,江南路众官员们循着笑声望去,只见总督大人与提司大人正言谈甚欢,内心放松之后更是暗生佩服,心想小范大人果非常人。众人暗自害怕地较劲局面竟是没有发生,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,让总督大人如此开心。
只见范闲又凑到总督薛清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。薛清面上微一诧异之后,顿生肃容,微怒之下点了点头,冷哼说道:“范大人勿要多虑。也莫看本官的颜面,这些家伙,我平日里总记着陛下仁和之念,便暂容着,范大人此议正是至理。”
范闲得了对方点头,知道薛清是还自己不在苏州落脚这个人情,很诚恳地道了声谢,然后缓缓站起身来。
……
……
范闲站起身来。绣棚里顿时安静了下来,此时河上天光透着竹棚,散着清亮,河风微凉,平空而生一丝肃意。
众人都看着他,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地就职宣言会如何开始。
“本官,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”范闲先看了一眼四周的官员们。笑着说道:“虽然与诸位大人往日未曾共事过,但想来我还有些名气。大家大约也知道一点。这性情,往好了说,是每每别出机,往坏了说,我是一个有些胡闹、不知轻重地年轻家伙。”
众官员呵呵笑了起来,纷纷说钦差大人说话真是风趣。真是谦虚。
范闲并不谦虚地说道:“那些虚话套话,我也不用多说了。陛下身体好着。不用诸位问安,太后老人家身子康健,京里一片和祥之意,于是咱们也不用在这方面多加笔墨。而诸位大人既然得朝廷重托,治理江南重地,这些年赋税进额都摆在这儿,沿路所见民生市景也不是虚假,功劳苦劳,也不用我多提……”
江南官员们都知道范闲一路暗访而来,闻得此语大松了一口气,只盼着范闲再多提两句,最好在给陛下地密奏上面多提两句。
不料范闲话风一转!
“不说诸位的好处,我却要说说诸位做地不对地地方。”范闲脸上依然微笑着,但棚子里却开始涌起一丝寒意,“似乎有些不厚道,但我依然要说,为什么?因为诸位大人似乎忘了本官的出身。”
范闲的出身是什么?不是什么诗仙居中郎太常寺,而是……黑糊糊、阴森森的监察院!众官员心头一惊,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,心想银子咱们都已经送到位了,您还想怎么样?监察院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!
“我自陆路来,沿路经沙州杭州,而那艘行船,却驶于大江之上。”范闲眯着眼睛,“听闻大江乃是一道银江,诸位大人往那艘船上送了不少礼物银两,还劳动了不少民夫拉纤……诸位大人厚谊,本官在此心领……只是如此光明正大的行贿,倒教本官佩服……诸位好大的胆气!”
不等众官员发话,范闲回身向江南总督薛清一揖,微笑说道:“今日见着本官之面,总督大人大发雷霆,当面直斥本官之非,本官不免有些惶恐,不明所以,幸亏总督大人体恤本官并不知情,直言相告,本官才知道,原来诸位竟是偷偷瞒着本官……做出了这等大胆的事来。”
他的声音渐渐高了,冷笑道:“监察院监察举国吏治,抓地便是贪官污吏,诸位却是大着胆子对本官行贿送礼……莫非以为我离了京都,这手中的刀……便杀不得人了吗?”
众官目瞪口呆,被范闲这番话震的不知如何言语,将求救的目光投向总督大人,发现总督大人却在捋须沉思,摆着置身事外的做派!
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,范闲先前那段话,说这些沿江官员是瞒着自己送礼,便轻松将自己提了出来,更是借口总督大人震怒,将总督大人摘的干干净净,还送了总督大人一顶不畏权贵,高风亮节的大帽子!
沿江送礼?你那属下也没拒绝啊!监察院信息通畅,你就算身在杭州,哪有不知之理?可是范闲此时硬称自己一无所知,这江南路地官员们当然也不可能硬顶,只好吃了这天大的一个闷亏,再看范闲地眼色便有些不对劲了———这范提司,果然如传言中那般,一张温和无害的清秀笑脸下。藏
着的是无耻下流与狠毒!
官员们不知道范闲接下来会做什么,下意识里吓地站了起来,傻乎乎地看着范闲。
只见他一拍手。掌声传出棚外,一名监察院官员手里都捧着厚厚的礼单,从京船上走了下来——礼单已经是这么厚了,那船上藏着的礼物只怕真地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!
范闲回身向总督薛清请示了几句。薛清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一幕,挥手示意衙门里的差役跟着监察院地官员上了般,不久之后,那些差役下人们便辛苦万分地拉着几个大箱子下了船,来到了竹棚之中。
几个箱子当众打开,只见一片金光灿灿!里面的珠宝贵重物品不计其数,统统都是沿江官员们送上来地礼物。
棚中风寒,所以生着火盆。范闲接过下属递过来的礼单,草草翻了几页,眉头微挑,笑着说道:“东西还真不少啊。”
众官员羞怒交加,心想钦差大人做事太不厚道,构织罪名,实在恶心。难道你还想治罪众官?除非你想整个江南官场一锅端了,总督大人到那时总不能继续看戏!你坏了规矩。得罪了江南官员,看你日后如何收场。
谁料到范闲接下来的动作,却让官员们的眼珠子险些掉了下来,只见他随手一抛,便将厚的礼单扔入了火盆中!
火势顿时大了起来,记载着众官员行贿证据的礼单迅疾化作灰烬。
范闲站在火盆旁沉默片刻之后。说道:“不要以为本官是用幼稚的伎俩收卖人心,你们没这么蠢。我也没有这么自作多情……之所以将这些烧了,是给诸位一个提醒,一个出路。”
他将双手负至身后,清秀的脸上闪过一丝坚毅之色:“本官乃监察院提司,不需要卖你们颜面,我在江南要做地事务,也不需要诸位大人配合,所以请诸位惊醒一些,日后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,休怪我抓人不留情。”
监察院可以审查三品以下所有官员,他敢说这个话,便是有这个魄力,至于颜面问题,他身份太过特殊,比任何一位朝官都特殊,所以确实也不需要卖,至于日后的事务配合问题……江南路官员的面子没了,难道就敢暗中与堂堂提司顶牛?
“呆会儿接风宴后,诸位大人将这箱子里的阿堵物都收回去。”范闲皱眉说道:“该退的都退了,至于役使的民夫,折价给工钱,那几个穷县如果一时拿不出来,发文到我这里,本官这点银子还是拿的出来地。”
众官员无可奈何,低头应是。
这时候,苏州码头上的滑索已经开动了起来,这个始自二十余年前地新奇玩意儿最能负重,只见滑索伸到了京船之上,缓慢地吊了一个大箱子下来,这箱子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东西,竟是如此沉重,拉的滑索钢绳都在轻轻颤动。
范闲事先已经查过数据,知道苏州港是负责内库出货的大码头,有这个吊装能力,所以并不怎么担心,而那些刚被他吓了一通的官员们,却是又被吓了一跳。
那个大箱子被吊到了岸上,又出动了十几个人才千辛万苦地推到了坡上,直接推到了竹棚之中,一位监察院官员恭敬请示道:“提司大人,箱子已经到了。”
范闲嗯了一声,走到了箱子旁边,箱子外裹柳条,里却竟似是铁做的一般。
众位官员心头纳闷,心想这位大人玩地又是哪一出?此时就连总督薛清与巡抚戴思成都来了兴趣,纷纷走上前来,看这箱子里藏的究竟是什么宝贝。
范闲自怀中取出钥匙,掀开了箱盖。
……
与第一次见到这箱子里内容地苏妩媚一样,棚内一片银光之后,所有的官员的眼睛都有些直了……银子!里面全是光彩夺目的银子!不知道有多少的银锭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!
其实先前那几个箱子里的礼物,贵重程度并不见得比这一大箱银锭要低,只是千古以降人们都习惯了用银子,陡然间这么多银锭出现在众人的面前,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。实在是太刺激了!
许久之后,众人有些恋恋不舍地将目光收箱子里收回来,都看着范闲。准备看他下一步地表演。
“这箱银子随着我从京都来到江南,日后我不论在何处为官,都会带着这箱银子。”范闲和声说道:“为什么?就是为了告诉各路官员,本人……有的是银子。不怕诸位笑话,我范安之乃是含着金匙出生的人物,任何想以银钱为利器买通我地人,都赶紧死了这份心。”
他接着冷冷说道:“此下江南,本官查的便是诸位的银子事项,一应政事,我都不会插手,不过如果有谁还敢行贿受贿。贪污欺民,可不要怪我手狠。”
“有位前贤深知吏治败坏的可怕后果,所以他带了几百口棺材,号称哪怕杀尽贪官,也要止住这股歪风。”范闲幽幽说道:“本官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地人,所以我不带棺材,我只带银子。”
众官员沉默悚然。
“箱中有银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两整。我在此当着诸位官员与来迎接的父老们说句话,江南富庶。本官不能保证这些银子有多少会用在民生之上,但我保证,当我离开江南的时候,箱子里的银子……不会多出一两来!”
范闲扫过诸位官员的双眼,说道:“望诸位大人以此为念。”
演完这出戏码之后,码头上的接风暂时告一段落。范闲坐回椅中,感觉袖子里的双臂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。心中暗自庆幸先前没有一时嘴快说出什么万丈深渊,地雷阵之类的豪言壮语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苏州地下午,总督府的书房里一片安静。
一品大员,江南总督薛清坐在当中的太
师椅上,脸上浮着一丝笑容,他的身边分坐着两位跟了他许多年的师爷,其中一位师爷摇头叹息道:“没想到这位钦差大人……果然是个胡闹的主儿。”
另一位师爷皱眉道:“殊为不智,小范大人这一下将江南官员的脸面都扫光了,虽然依他地身份自然不惧此事,但总显得不够成熟。”
薛清微笑说道:“二位也觉得他这一番卖弄有些做作?”
二位师爷互视一眼,点了点头。
薛总督叹息道:“年轻人嘛,总是比较有表演欲望的。”
师爷小意问道:“大人以为这位小范大人如何?”
薛清微微一怔,沉忖半晌后开口说道:“聪明人,极其聪明之人,可以结交……可以深交。”
师爷有些诧异,心想怎么和前面地结论不符?
薛清自嘲地笑了笑:“做作又如何?这天下百姓又有几个人能看见当时情景?京都的那些书阁大臣们又怎么知道这月里的真实情况?传言终究是传言,人人口口相传里,总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由自己对事实进行一些符合自己倾向的修正。”
“小范大人在民间口碑极佳,百姓们传播起此事自然是不遗余力,因为对他的喜爱,就算此事当中小范大人有些什么不妥之处,也会被那些口语抹去,忽视,而对于不畏官场积弊、当面呵斥一路官员的场景,自然会大加笔墨……”
“哈哈哈哈。”这位总督大人快意笑道:“箱藏十万两,坐船下苏州,过不多久,只怕又是咱大庆朝地一段佳话了,这监察院出来的人,果然有些鬼机灵。”
另一位师爷百思不得其解说道:“既是聪明人,今日之事明明有更多好地办法解决,为什么小范大人非要选择这么激烈而荒唐的方法?”
总督薛清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:“你知道什么?”
他闭上嘴,不再继续讲解,有些事情是连自己最亲密的师爷们都不应该知道的。范闲今日亮明刀剑得罪了整路官员,何尝不是在向自己这个总督表示诚意?对方抢先言明要住在杭州,就说明对方深明官场三味,而将这些官员唬了一通后,今后钦差在江南,官员们也不会去围着钦差,自己这个总督依然是头一号人物。
薛清忽然想到另一椿事情,眉头不由皱了起来,对于范闲的评价更高了一筹——这名年轻权臣今日如此卖弄,只怕不止是向自己表示诚意那么简单——由春闱至江南,这范闲看来是恨不得要将天下的官员都得罪光啊,这两年朝中大员们看的清楚,范闲连他老丈人当年的关系也不肯用心打理,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要做孤臣?
薛清身为皇帝亲信,在朝中耳目众多,当然知道关于范闲的身世流言确是实事,一想到范闲的身份,便顿时明白了对方为何要一意孤行去做个孤臣。
这是防着忌讳。
薛清叹了口气,摇了摇头,心想大家都是劳心劳力人,看来日后在江南应该与这位年轻的范提司好好走动走动才是。
……
……
下午的暖阳稍许驱散了些初春的寒意,苏州城的人们在茶楼里喝着茶、聊着天,苏州人太富,富到闲暇的时间太多,便喜欢在茶楼里消磨时光,尤其是今天城里又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,更是口水与茶水同在楼中沸腾着。
人们都在议论刚刚到达的钦差大人,那位天下闻名的范提司。
“听说了吗?那些官员的脸都被吓青了。”一位中年商人嘿嘿笑着,对于官员们吃瘪,民间人士总是乐意看到的。
另一人摇头叹道:“可惜还不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?我看钦差大人若真的怜惜百姓,就该将那些贪官污吏尽数捉进牢去。”
“蠢话!”头前那中年商人鄙夷嘲笑道:“官员都下了狱,谁来审案?谁来理事?小范大人天纵其才,深谋远虑,哪会像我们这些百姓一般不识轻重?这招叫敲山震虎,你瞧着吧,好戏还在后头,我看江南路的官员,这次是真的要尝尝监察院的厉害了。”
那人点头应道:“这倒确实,幸亏陛下英明,将提司大人派来了江南。”
商人压低声音笑道:“应该是陛下英明,将提司大人生出来了。”
茶桌上顿时安静了下来,片刻后,爆出一阵心照不宣的轻笑。最后那名商人说道:“先前我店里那伙计去码头上看了……提司大人下手是真狠,那些坐着大船下江的手下,硬是被打了三十大鞭。”
对面那人回的理所当然至极:“这才是正理,虽说是下属瞒着小范大人收银子,但罪过已经摆在那里,如今银子退了,礼单烧了,不好治罪,但如果不对下属加以严惩,江南路的官员怎么会心服?先前我也去看了,啧啧……那鞭子下的真狠,一鞭下去,都似要带起几块皮肉来,血糊糊的好不可怕。”
而在钦差大人暂时借居的一处盐商庄园里,一处偏厢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嚎之声。
范闲看着被依次排开的几个亲信,看着对方后背上的道道鞭痕,将手中的伤药搁到桌上,笑骂道:“不给你们抹了,小爷我体恤下属,你们却在这儿嚎丧……挨鞭子的时候,怎么不叫惨点儿?也不怕别人疑心。”
苏文茂惨兮兮地回头说道:“要给大人挣脸面,挨几鞭子当然不好叫的……不过大人,你这伤药是不是有问题?怎么越抹越痛。”
范闲笑了起来,说道:“鞭子打的那么轻,这时节当然要让你们吃些苦头!”
他起身离开,一路走一路摇头,心想万里说的话有时候是正确的,自己不是一个好官,也不好意思要求手下都是清吏,这上梁下梁的,还真不好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