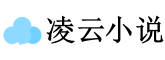“林兄弟,我当然知道你志向高远,品性正直。如果是我大华姊妹,我老高绝不会干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。可是,她是突厥女人啊!突厥人蹂躏了我们多少的大华女子?这个血海深仇,何时才能得报?!抢突厥的女人,那能叫抢吗?!这是每个正直的大华男人的分内之事,是为我大华姊妹报仇、为大华万民争光啊!”高酋义愤填膺,口水漫天飞舞。
“抢突厥女人不叫抢?太好了——哦,不,高大哥你听错了,我说的是太早了!”林大人急忙改口,面色严肃道:“我的意思是,怎么着也要等打到突厥王庭,推翻毗迦可汗的暴力统治之后再动手抢嘛。我们的理想要远大些——高大哥,那突厥女人你藏在哪里?我这就找她报仇去!!!”
“本来是应该将她拿回来的——我们搜到一处民宅时,已经发现了进城时看到的那女奸细乘坐的马车。”高酋叹了声,懊悔道:“可是杜修元这死脑子,定说大帅军规,不准抢夺百姓财物,违者军法处置。还没进院子,他就将我阻了下来,你说可不可气?我们是抢女人,和抢财物完全是两码事嘛!林兄弟,你可得好好教教杜修元,他的灵活性要是能赶上你的万分之一,他打胡人就是必胜了。”
原来还没有捉到“月牙儿”啊,林晚荣长长吁了口气,心里略略有些失望,拍着高酋肩膀道:“高大哥,杜修元说的也有道理,强抢民女毕竟是不好的,我们都应该谴责这种暴行。不过,如果那民女是奸细,就应该另当别论了。可是,你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那,不能因为人家长得漂亮,你就说人家是奸细吧!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,我们讲求的是以德服人。”
要证明她是奸细?高酋嘿嘿道:“这还用证明吗?!兵荒马乱的,要是正经人家的女子,谁会让她头露面,在这危险境地出没?唯有女奸细,才有这个胆量,也才有这个必要——你瞧她那俏模样,眼神一勾,就足抵千军万马了。她要不是奸细,那还有天理吗?!”
“哦,是吗?”林晚荣微微点头:“好像有些道理。不过,我们的大军是纪律部队,没有证据,不能随便栽赃罪名。”
看林兄弟似乎不为所动,高酋急急拉住他,挤眉弄眼道:“兄弟,战时非比寻常,今夜发生这么多变故,连元帅都差点出了意外,而那女奸细又凑巧这个时候在城里出现。要说巧,这也太巧了吧!防患于未然还是很必要的!就算她不是奸细,那咱们也不能让一个纯洁天真的弱女子流落战火之中啊。看着一朵鲜花凋零,这是多么大的罪过阿,林兄弟,你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,怎么忍心干出这种残暴的事情呢?!这不是你的风格啊!”
“罢了,心软一向是我最大的毛病。”林将军长长叹了口气:“我就和你看看去吧。若她真是奸细,就把她拿回我帐里好好审问!若是胡人的良家女子,那就让她赶紧走路,这炮火无情的,要是伤到了脸蛋,她的父母该多着急啊!万一她一时半会找不到家人,我也唯有秉着人道主义救援原则,先暂时收留她了——咦,高大哥,你瞪着我干什么,怀疑我的人品么?!暂时收留而已,不是收房。”
高酋挤眉弄眼,抱拳嘿嘿笑着,神情说不出的猥琐:“既如此,我就替那突厥女人,感谢林将军的大恩大德了。唉,像林大人这样正直的人,我真是一辈子也没见过,这突厥女人也不知走的什么运气,竟然遇见了您!”
两个人同时龌龊大笑,当下便由高酋带路,林晚荣带了亲兵,一起擒那女奸细而去。
兴庆府战事连连,城内人烟稀少,今夜出了胡人刺杀李泰之事,大军正在四处搜查,城内早已经不复往日里的宁静。
高酋七拐八摸,在临近城北大门的一处小巷子边上停了下来,四处打量了几眼,压低声音小心道:“林兄弟,到了。那突厥女奸细,就藏在前面的民房里。”
林晚荣抬眼往前看去,这巷子里漆黑隆冬,道路都看不清晰,两边的墙壁或倒或断,早已残败。离着自己五六十丈的远处,一座土墙筑成的院落里,微微闪烁着灯光。那院子占地宽广,中间停着几辆马车,旁边堆积着货物,时时有马嚏声传来,正是今日进城时瞅见的商队,“月牙儿”看来就在这里不假了。
杜修元带了人马,正潜藏在暗处守候着,见林晚荣来到,急急窜过来道:“林将军,你可来了。”
林晚荣点点头,神色肃穆:“杜大哥辛苦了。方才我正在营中处理军务,高大哥回来禀报,说这里情形古怪,可能藏有重要的胡人奸细,极大的威胁着元帅的安全。我不放心,就来看看了。里面的情况怎么样?有多少胡人,有无强弓利弩?你不要担心,我已经调动了神机营的神箭手百名、火炮五门,另有步营三千,一起前来协助你,眼下各路大军已在路上,片刻即到。”
又是神箭手又是火炮的,叫林大人这么一描述,那情形还真是严重之极了,杜修元听得暗自咂舌,忙瞪了那“谎报军情”的高酋一眼。老高被扣了屎盆子,却不能争辩,唯有嘿嘿干笑两声,表示歉意。
“禀将军,这院子里住的,就是我们进城时看见的那商队。共有驼马十匹,马车五辆。由于不敢打草惊蛇,因此里面的总人数尚是不详,但依末将估计,绝不会超过三十人。这些人以大华人居多,未见配有兵刃,也未流露出明显的奸细特征。是否胡人派出的奸细,还有待查证。”
杜修元将里面的情形大概描述了遍,林晚荣点点头,赞道:“杜大哥,办的好!若真的就只有三十余人,那神机营看来是用不着了——”
就这么大的个院子,撑死了能藏多少人?杜修元抱拳稳稳道:“即便院内全是奸细,末将也有足够信心应付,不需再调人马相助,请将军放心。”
“那好,神机营和步营就不调了,”林晚荣嘿嘿道:“就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吧。今晚元帅遇刺,对我军影响甚大。因此,对城内的每一个胡人,尤其是漂亮的胡人,绝不能放过,一定要仔细盘查。”
杜修元应了声,便带领兵士将那宅子围了,高酋一马当先的冲在最前,将那宅子的大门拍得哗哗乱响,怒声喝道:“开门,开门,官军查房了!”
兵士们的刀枪哗啦作响,惊得院里的骡马受惊嚎叫起来,四面一片沸腾。
等待片刻,自门缝里传出一个颤抖的声音:“大人,我们是陇西的商队,到塞外做生意的——”
“少废话!”高酋等的不耐,不待他说完,便一脚踹开那大门,数百军士如洪水般拥入,熊熊火光映照着明晃晃的钢刀,将那开门的商贾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闻着院子里的声音,屋里歇着的大华商贾们早已披衣起床,望见高酋与杜修元带领兵马、杀气腾腾的闯入,那钢刀便架在众人面前,商贾们顿时面色苍白,浑身如筛糠般颤抖。这些大华商人中间夹着几个突厥人,虽亦是衣衫凌乱,神色却是镇定了许多。望见大华诸商惊慌失措、瑟瑟发抖的样子,他们眼里顿时闪现出几分轻蔑神色。
高酋哗啦一声拔出佩刀,怒号起来:“官军查房,有衣裳的穿衣裳,没衣裳的披麻袋!现在听我口令:男人在左边,女人在右边,骡子站中间——”
他脸膛黝黑,牛眼如铃,生的凶神恶煞般,不说大华商贾,就连那几个突厥商人也不敢与他对视。“高大哥好气势!”连杜修元也忍不住赞他一声。
高酋洋洋得意的嘿嘿几声,再转过头去却有些傻了。那骡马左边站满了人,右边却是连个母蟑螂都没有。
“咦,”高酋顿时恼了,钢刀一挥,火道:“人呢,就只有这么几个吗?女人,啊不,奸细呢,长得很漂亮的奸细呢?”
那开门的商人四十来岁模样,似是这商队的头目,见这位官人挥舞着钢刀要杀人,他忍了心中恐惧,抱拳小心道:“大人,什么奸细?!天大的冤枉啊!我们都是陇西府正经的商人那。您看,我身上还带着陇西府的批文呢。”
杜修元接过批文扫了几眼,点头道:“你说你是陇西府经商的,那他们呢——”
他朝那几个突厥人扫了一眼,冷哼几声。领头的商人忙道:“大人误会了,这几位是草原来的友商,也是突厥内部的反战人士,您看,陇西府也有批文的!”
他又从身上掏出盖了官印的信笺要递过来,高酋眼一瞪,将那批文抢过,扔在地上踩几脚,怒道:“批文?批文有个屁用,老子看圣旨都看不过来。我问你,你说的什么突厥友商、反战人士,就只有这么几位么?!”
头领点点头:“目前就只此几位了。”
“没有女人?!”
头领犹豫片刻才道:“没有。”
林晚荣跟在高酋和杜修元身后冷眼旁观,见高酋问话之时,那几个突厥人眼神闪烁,目光不断向内屋的帘子里瞄去。那帘子轻轻晃动,似是掩藏着什么。
“没有?!”高酋钢刀一挥,正要发飙,林晚荣笑着拉住了他:“高大哥,你忘了么,我们说过的,以德服人!!”
这个时候要以德服人?高酋冷汗淋漓。林晚荣朝那帘子里指了指,笑着喊道:“喂,里面有人吗?!”
几个突厥商人脸上的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,双拳紧紧握住。
望着那晃动的帘子,高酋也省悟了,嘿嘿一笑,凑到林晚荣身边道:“兄弟,人家是突厥人,听不懂咱们大华话,该用突厥语才是。喂,那老头,里面有人吗,这句用突厥语怎么说?”
他说的那老头,就是指那商人头领,那商贾叽里呱啦翻译一阵,高酋听得直晃脑袋,满是期冀的目光盯着林晚荣:“林兄弟,你这么聪明,这一句突厥话肯定不在话下了。”
“不就是突厥话么?简单!”林大人打了个哈哈,眼皮子也没眨下,朝那帘子里字正腔圆喊道:“里面,人的,有?出来的,干活!”
高酋呆了呆,忽地大喜:“林兄弟,你真聪明。这突厥话真的很好懂,我都能听懂一半呢。”
“突厥”话也喊了,那帘子里却沉默的连一根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见,林晚荣哼了声,换成大华语冷道:“我数到五,你再不出来,我就派人直接杀进去了。高大哥,准备——”
还要数到五?林兄弟太仁慈了,高酋正在感叹,就听林晚荣大声道:“五!!!弟兄们,冲啊!”
原来是这么个喊法,高酋满身大汗,稍微愣了一下,杜修元就已冲到了他前面。数十名士兵冲入房内,没有刺耳的刀枪撞击声,更没有想像中的惊呼,屋里安安静静,连落下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。
“怎么回事?!”望着杜修元垂头丧气的走出来,林晚荣有些吃惊。
杜修元低头小声道:“将军,没有人!”
没有人?!林晚荣掀开帘子,缓缓踱进屋里。这是一座土跺围成的内屋,屋里陈设简单,黄泥盘成个土炕,炕上放着一张小茶几,收拾的整齐干净,看不出一丝的灰尘。果真没有人!可是这明明就是“月牙儿”所在的商队,怎么可能不见了这突厥少女?林晚荣眉头紧锁,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空气中隐隐飘过一丝淡淡的幽香,似是春晨的雾般不着痕迹。他用力嗅了嗅,脸上忽起惊愕之色,这味道再熟悉不过,正是名扬大华的林氏香水。这茉莉香型的香水,怎么会出现在塞外大漠?难道是“月牙儿”带过来的?如此看来,那突厥少女一定在这房间里驻足过。没想到,林氏香水都已经传到突厥去了,林晚荣摇摇头,不知是悲是喜。
“将军,你看,那是什么?”杜修元带人仔细搜索,在土炕的枕旁,忽地发现了一个物事。那东西由七根手指一般粗细的竹节紧紧粘连在一起,长短高低各不同,各节中间挖孔,孔眼的位置却又不同。
林晚荣拣起这东西,抚摸了几下,又缓缓凑到嘴边,轻轻吹了口气,这竹节嘟的发出一声脆响,甚是悦耳。
杜修元奇道:“原来是门乐器,这玩意儿我倒没见过,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。”
林晚荣笑了笑,双手交叉,按住几个孔眼,便有几声长长的翠笛跃出,抑扬顿挫,煞是好听。
“咦,兄弟你还会吹箫?!”高酋走了进来,奇道。
林大人咬着牙哼了声:“吹个屁的箫。这玩意儿叫做玉笳,乃是草原上的一门乐器,吹奏这玉笳,学名叫品玉。吹箫那样的高难度活,我不会!”
嘴角似有淡香飘过,隐隐还有细腻的感觉,他低头看去,却见那玉笳的竹管口上,隐隐残留些胭脂淡红,在那竹排上,正勾成一个浅浅的月牙儿。
这玉笳竟是“月牙儿”用过的!林晚荣嘿了声,她吹了我吹,相当于吻别!只是不知那丫头是不是初吻?
没有捉到美丽奸细,高酋垂头丧气,一把将那领头的商贾拉进来,怒道:“说今天跟你们一起进城的那突厥女人哪里去了?”
那商人恍然大悟:“大人,原来您说的是她啊。”
林晚荣悠悠道: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
看杜修元和高酋对林晚荣的态度,也知这位是大人物了。那商贾不敢怠慢,急忙道:“她的名字,小人也不清楚。这位姑娘是中途一个胡商介绍来的,身边还带着几人,她一路除了微笑外,很少说话。她们今日在此歇息到傍晚时分,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。听那口气,好像是这位姑娘想家了,要连夜赶回草原去。”
这么说,月牙儿在封城之前就已经走了?!林晚荣哦了声,望着那玉笳上的唇印,一时有些发愣。